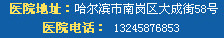众所周知,在中国辽阔的疆域里,有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可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还有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需要捍卫和守护。
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海洋文明的探索从未止步。在古代,有一批批无畏的开拓者发现商机,远渡重洋,与大海搏斗,有的人成为了将中华文化远播海外的先驱;另一些人则葬身海底,千百年后,尸骸已被海水荡涤不知所踪,但货物和船只却留下来,在海底无言地叙说着一段辉煌而悲壮的历史。
他们把勇敢者的基因传了下来。今天,在中国考古界,有一支专门从事水下考古的队伍,他们在悠长的海岸线上寻找着遗失千年的历史记忆,潜入黑暗的深水,让沉睡海底千年的船只和宝货重见天日。在打捞发掘出的战果里,有一艘南宋沉船像明珠一样镶刻在水下考古的版图上,它的名字叫“南海一号”。
孙键是现任“南海一号”考古队的领队,他和许多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一起见证了这艘船从定位、打捞到发掘的曲折过程,更见证着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的三十年。
“中国水下考古是在外部鞭策下诞生”
孙键今年53岁,他已经习惯了北京、广东两个工作地点来回跑。北京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所在地,在这里他的身份是坐在办公室的技术总监;广东坐落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这里他又成了穿着工作服、在发掘现场有条不紊指挥的“南海一号”考古队领队。今年十月份,“南海一号”正式开始了最后一次的发掘工作。在发掘的间隙,孙键赶回北京,参加《国家宝藏》的录制。临上台前,他和我们轻松说笑。我们好奇:“您不紧张吗?”他笑笑说,做水下考古,第一就是心理素质要过硬。比起他在水下经历过的复杂情况来说,这种场面还是能从容应对的。
大部分人都对“水下考古”的工作形态很陌生,听上去像是去海底探险和挖宝。面对着这种误解,孙键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澄清,水下考古其实是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一种考古手段,是陆地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工作内容不仅面向海洋,也包括内陆的水下遗址,比如沉没在水下的古均州城。当然,不管是内水还是海洋,潜水是必要的技能。孙键从年参与水下考古开始,至今下水也有上百次,算是极有经验的老手,但水下的情况却很难预测。尤其是打捞古代沉船,有沉船往往就说明水况复杂,台风、泥沙、氧气、渔网、海蜇或任何的疏忽都可能成为威胁。
他跟我们描述过其中一次危险情形。那一次是他进行单人作业,却在水下被渔网缠住背部,周围一片漆黑,渔网无法挣脱。“我看了下氧气瓶,完了,我只能活四十分钟。好在当时没慌,就在海床上刨坑,给自己挖出一个周转的生存空间,把气瓶、背心都解开了。呼吸管是有一定长度的,我就攥着那个咬嘴慢慢往上走。提到半空被拉住了,但那个空间已经有能见度。我赶紧用刀把缠住的地方切开,跑远点,确认没有渔网,再把装备穿上。”
广东西樵山古代采石场水下调查
但孙键说,这份危险并不是水下考古工作本身带来的。只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小心谨慎的工作态度和从容不迫的心理素质,这些危险是完全能够被避免。那个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为何孙键说水下考古,心理素质是第一位的。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水下作业还安排了“潜伴”制度,两个人一组下水,一个人有危险,另一个人要帮忙救援。“只有当你握着潜伴手的时候,才明白,水下的生死与共,性命相托,两个人下水就要两个人一起上来。”孙键告诉我们,“三十年了,直到今天,中国水下考古没有发生过一例重大安全事故。这个数字是团队协作的结果,值得所有水下考古人骄傲的。”
孙键是从年开始参与水下考古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80年代末,英国人米切尔·哈彻在中国南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驶离广州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哥德瓦尔森”号商船,自行盗捞后委托佳士得公司在荷兰拍卖。短短10天,佳士得将23.9万件属于这条沉船的中国文物卖出了多万美元。而国家文物局派去想买回部分文物的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因为身上仅携带了3万美元,甚至都未能举起手中的拍卖牌。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两位陶瓷专家。回国后,他们就给国家文物局递交了报告,希望立刻发展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守护好在中国水域内的水下文物。国家文物局将此事委托给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在俞先生的鼓励下,孙键决定投身于这项新兴的考古事业。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他经历了几乎所有中国重大的水下考古项目,比如“南澳一号”明代沉船、“南海一号”宋代沉船、古均州城水下考古调查等等,在这里面,他觉得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这艘“南海一号”。
年南海一号水下调查
(左起崔勇,朱滨,楼建龙,孙键)
“南海一号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一张名片”
“南海一号”,可能是中国水下考古人感情最深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水下考古的开拓者俞伟超先生取的。这艘船,无论在年代、船体大小、保存情况等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目前沉船中的No.1。但最重要的是,俞先生说,“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着一个开始。”所以这个“一号”,它当之无愧。它在年被广州打捞局意外发现,但这个发现,令人又喜又忧。喜的是这艘沉船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专家认为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忧的是当时中国水下考古技术尚在萌芽,还无法承担这么大体量的发掘工程。于是,“南海一号”的打捞计划被暂时搁置。俞伟超先生临终前,还在惦记着这条船,为它写下绝笔寄语:“商船战舰,东西辉映。”
这一搁置,就是二十年。二十年间,中国水下考古迅速发展壮大,从当初十几个人扩展到一百多人,无论是器材装备还是技术能力都有了长足进步。终于,在年,“南海一号”躺在海底静静等待了二十年之后,中国水下考古准备好了,“南海一号”等到了它的出水之日。
但到底如何出水?这是一个当时打捞局和文物局争论了很久的问题。孙键回忆说,最终定下整体打捞的方案,是经过了好几轮激烈辩论的,因为整体打捞技术在外国都没有过先例。要如何把这么大的沉船整个捞上来,大家心里都有些没底。国外的通常做法是在水下分解船体,再捞上来;但孙键认为,对于一条沉船,最重要的文物不是船上的货物,而是这条船。只要能够被整体打捞,这条船上当时人们的生活痕迹就会被完整地保留,我们就能知道在千年前,一艘出海航行的船上,人们吃的什么肉,喝的什么酒,用的什么调料,带的什么家畜。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研究材料。
经过了周密的设计,克服了淤泥的阻力与海底泥沙的冲刷,广州打捞局最终在年12月21日,用起吊能力吨的“华天轮”号将“南海一号”打捞出水。
“华天轮”号将“南海一号”打捞出水(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中国海洋施工能力的胜利。对于这艘船的文物发掘来说,整体打捞方案是非常成功的。”孙键由衷地赞叹。接下来,这艘沉船就被运到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模仿它原来的海水环境,使它长久保存。到这儿,接力棒就交给了孙键带领的考古发掘团队。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在水晶宫内的室内发掘,解开这艘八百年前古沉船的秘密。孙键介绍说,“在这条船上,我们相继发现了牛羊的骸骨、橄榄、胡椒、甚至是一坛子腌的咸鸭蛋,这些生活痕迹如果在水下拆解发掘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全世界唯一一条,可以在精准控制环境下发掘的沉船。”
所以,可以说“南海一号”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如今它也成为了一张值得骄傲的名片。这样大的工程是几代水下考古人接力完成的,从开拓者俞伟超到后继者孙键,再到更年轻一辈的水下考古人,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幅蔚蓝色的中国水下文化遗址版图徐徐展开。
“作为水下考古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孙键的身边,也有一批年轻的后辈,他们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进行时”,更是“未来时”。主持发掘致远舰和经远舰的周春水,还清晰地记得在水下发现带有“致远”铭文的瓷盘和刻有“经远”两字的木牌,确认它们就是当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被击沉的致远舰和经远舰的时刻,两百年前那段悲壮的历史扑面而来,仿佛激烈的战斗场面又重现眼前。
从事海岸线考古的杨睿解释说,水下的文物其实是一颗时间胶囊。水就像琥珀一样,能隔绝人为的、自然气候的影响和破坏,它会裹挟着泥沙把历史的重要瞬间凝结在海底,从而能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这是文献资料所不能代替的。
参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水下调查的梁国庆描述道,当水下发现或者摸到了东西的那一刻,那种巨大的惊喜感和成就感,想要嗷嗷叫喊,却说不出话,只能吐几个水泡来表达。正在水晶宫内参与“南海一号”最后一次发掘的石俊会说,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以前水下考古工作都要去请媒体来采访报道,而发掘“南海一号”时,想去现场采访的媒体太多,要通过申请才能获得采访机会。这说明水下考古正在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
当然,这份工作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孙键一年中2/3的时间都在海上。在海上“漂泊”过的人都深知其中的艰辛,最长的一次,他在海上呆过三个多月。梁国庆也提起过对于家人尤其是妻子的愧疚。“有的时候我一年只能回家待两三个月,我老婆刚开始也因为这个闹过别扭,但是她看我也不会放弃这个职业,就慢慢理解我了,也支持我了。”“下个月,我的第一个小宝宝就要出生了。”梁国庆忍不住露出喜悦,“要是没有家人们的支持,我觉得中国水下考古不会走到今天。”
节目播出时,梁国庆的宝宝已经出生
肖达顺和胡思源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批人。他们说,自己非常幸运,赶上了一个水下考古的好时代,见证着前辈们披荆斩棘、水下考古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投身其中,与有荣焉。这群年轻人都是考古专业出身,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由从陆地考古转向了水下考古,能够承受工作的艰苦条件和或长或短与家人的分离,是因为对这份事业真心的热爱。
除了人才建设,孙键认为,对于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当下最重要也是最急迫的工作是“摸清家底”,弄清楚到底在中国水域内有多少处水下文化遗址。这个数字在年是处,到今年已经超过处,探索还在不断继续。之前,几乎所有的水下考古项目都是跟在盗捞贼后面进行抢救性发掘。孙键至今谈起那次“碗礁一号”的发掘仍然非常遗憾和痛心,“那是我见过水下瓷器最好的一条沉船,我们当时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发现沉船的结构保存得都很好,我甚至能摸到摆放货物的货架和船的仓壁板,特别遗憾的是我们在第二年准备再去,这条船就被盗捞破坏掉了。因为盗捞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多的利益。所以就把船整个毁掉了。”这件事使孙键意识到,只有尽快摸清家底,加强公众对水下考古工作的认识和参与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水下的珍宝。
国家文物局领导在南澳I号水下考古发掘现场视察工作(第二排左起第四位为孙键老师)
今年是我国水下考古成立的第三十个年头。我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支百余人的人才队伍,潜水设备也已经与世界一流比肩。如今的中国可以自信地说,目前水下考古的水平足以守护任何一座发现在中国海域内的水下遗址,当年耿宝昌、冯先铭两位先生的遭遇,再也不会发生。而回头望的时候,孙键感慨道,“其实我们的水下考古起点是很高的,绝大多数水下考古专业人员都经过正规大学训练,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素养;更重要的是有国家(国家文物局)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与推动,前辈学者们的高瞻远瞩与提携帮助,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与付出,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因为我国的海岸线很长,在这条海岸线上发生过太多的历史事件,水下也有很多珍贵的文物等待我们去发掘,这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任务。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水下考古的行列之中。”
三十年的艰辛与荣光,都已被载入史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水下考古人,接力还在持续。中国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1.8万千米的海岸线,无数水下珍宝,正等着我们一一点亮。
撰稿
许雪菲
编辑
江菁菁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4443.html